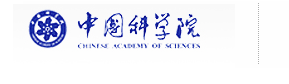|
怀想饥饿
张小平
年岁渐增,收入渐高,菜篮子日见丰富,餐桌上的佳肴品种丰盛,鱼肉禽蛋已属平常,山珍海味偶尔也能尝鲜,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、水里游的变着花样端上桌,烹、炒、煎、炸,酸、甜、麻、辣,红烧、白煮、清蒸,大快朵颐之后,无须打肿脸充胖子,身上也敲不到嶙峋的风骨了。可惜胃不够争气,竟常有饱胀的感觉,吃嘛嘛不香,怪不得过去老人们常说:“饥最好吃!”从而怀念起饥饿的感觉来,甚至贱到认为饥饿的感觉真的很好。
说到饥饿的感觉,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并不陌生。小时侯饥饿就像魔鬼一样时时纠缠、困扰着我以及我的父老乡亲,而我能做的就是把能找到的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塞进嘴里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如今见到食物仍吃出饱嗝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筷子。
小时侯,一饭一粥来之不易,母亲在锅里加入了大量青菜、萝卜之类,但充饥效果不如人意,顿顿吃到嗓子眼,转一圈又饿了,因此总召来家长的责骂:“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吃,肚子里像长了牙齿,生铁都消化得了。”骂归骂,还得吃。哪怕是嚼上一块生咸菜,喝上一碗水暂时充实一下辘辘饥肠,也成了一种惬意的享受了。
那时侯,家长白天都出社工,我们也乐得无拘无束,很少窝在家里的,村子里,田野上,树丛中,到处有我们活动的身影,出得门来,就像饿饕一样一边游荡一边四处搜寻“猎物”。
晚春,我们学着电影中的游击队员,东瞅瞅西望望,确保“平安无事”后,伺机潜入队里的农田,摘蚕豆,剥豌豆,哪怕只有小拇指指甲篷儿大,一包水,也会毫不犹豫地填进嘴里;即便苦涩,也会毫不犹豫地咽下去。初夏黄昏,三五顽童,寻个僻静处,田埂上用铲草的小锹挖个坑,摘几根麦穗,扯几根枯草,和在一起点燃了,烧一烧,甭管熟不熟,扒出来,放到手上揉一揉,吹一吹灰,捂到嘴里大嚼,吃得半脸灰满嘴黑,但那份满足绝不比如今孩子吃肯德基逊色,口齿留香,余味绕梁。到得盛夏时节,我们的肚子都是鼓鼓的,为啥?撑的。这在当时很是难得,因为垛子上的瓜熟了。正午时分,天热人困,看瓜的麻老爹在看瓜舍前的凉棚里“烀猪头”(方言,男人睡熟,鼾声如雷),我们假装下河洗澡(游泳),从大河里潜入垛上,身子紧贴着地皮摸到垛子上瓜地里,不管生瓜还是熟瓜,不管是水瓜、团瓜,还是“奶奶啃”、牛角瓜,看到一个摘一个,摘上两三个就赶紧回头。被麻老爹发现了也不打紧,他是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,能骂会发狠,一般不追。秋季,也不挨饿,地里的山芋、水里的菱角,对我们来说,就像现在的孩子吃冰箱里的火腿肠一样方便。冬天,不敢到外面乱窜,天寒地冻的,身上衣衫单薄,只好围着小铜炉,烘手的同时炸几粒蚕豆儿,黑黑的烧蚕豆放到嘴里“嘎嘣嘎嘣”地咀嚼,很有成就感。
时光真是奇妙,童年的苦涩经过岁月的沉淀、时光的过滤留下的竟然是美好的回忆,真是怪了,不知这是不是“好了疮疤忘了痛”?当然,回忆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!
(张小平现就职于江苏省兴化市顾庄小学。本篇为所外来稿。)
|